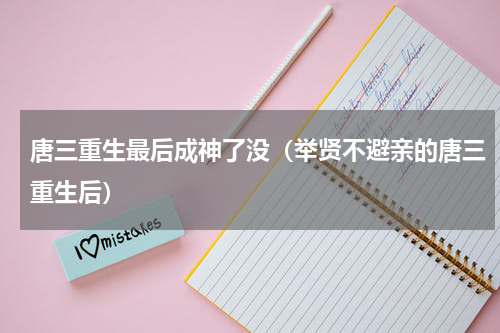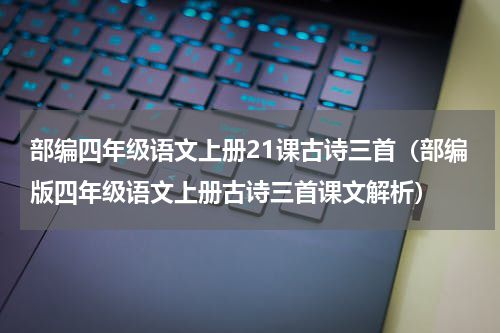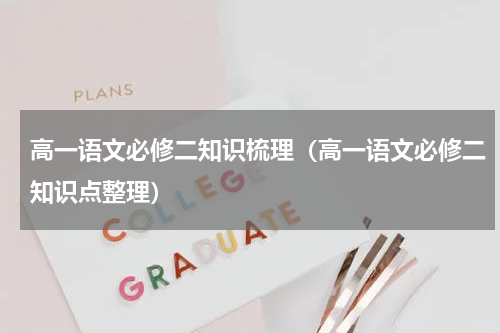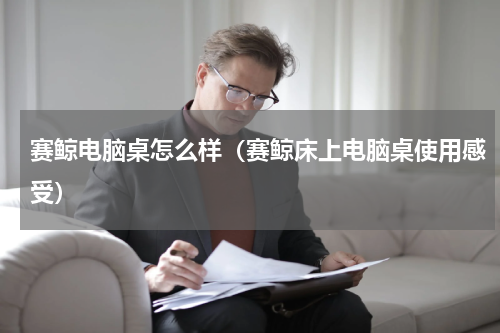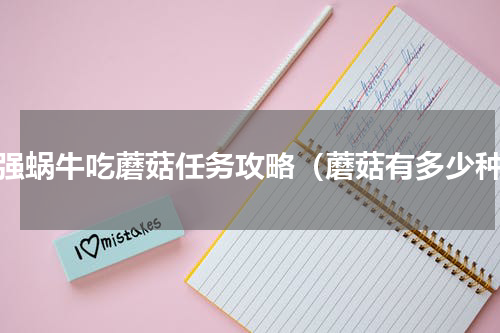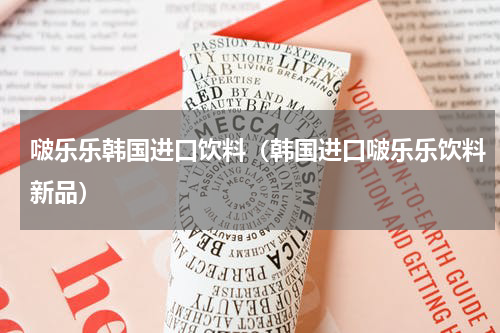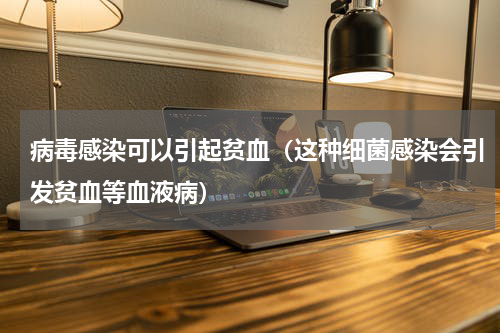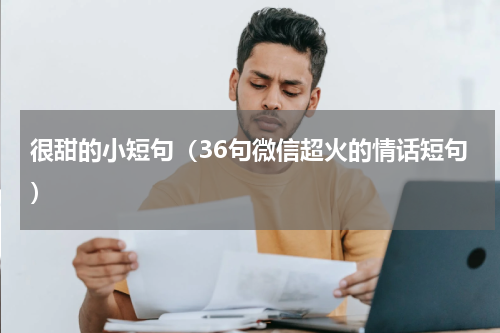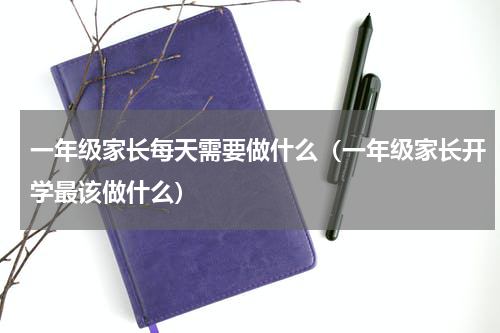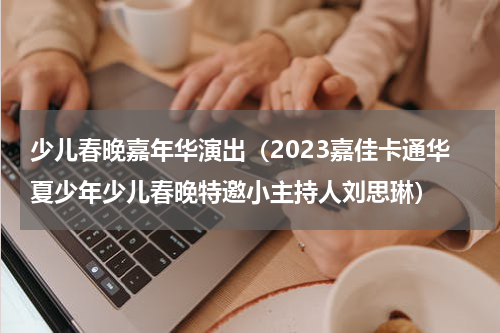作者君子九思两湾似蹙1非蹙罥烟眉2,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。态生两靥之愁3,娇袭一身之病4。心较比干多一窍5,病如西子胜三分6。5比干:商纣王的叔叔,因强谏被杀。6西子:即西施,春秋越国战败后送给吴王的美女。传说其患心痛病,《庄子·天运》有“故西子病心而颦其里”。以列藏本文字为最佳。黛玉的愁怅来自打小的体弱多病,也来自幼年的丧母之痛,更多的则是来自与生俱来、多愁善感的敏悟。

作者 君子九思
两湾似蹙1非蹙罥烟眉2,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。态生两靥之愁3,娇袭一身之病4。泪光点点,娇喘微微。闲静似姣花照水,行动如弱柳扶风。心较比干多一窍5,病如西子胜三分6。
[注释]
1蹙:唐代僧人慧琳在《一切经音义》解释说:“颦蹙,忧思愁不乐之貌也;《考声》‘聚眉也’。”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有“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”,宋代朱熹对此作了注解:“蹙,聚也。頞,额也。人忧戚则蹙其额。”
2罥(音绢)烟眉:“罥”,原指捕鸟兽的网,引申为“挂”(《玉篇·网部》)。罥烟眉,当指浅淡、纤细的眉毛。曹雪芹友人敦诚《晓雨即事》诗有句:“遥看丝丝罥烟柳”。
3靥:颊辅,嘴角边的微涡,就是笑涡、酒涡。曹植《洛神赋》有“明眸善睐,靥辅承权”句。
4袭:继。江淹《始安王拜征虏将军丹阳尹章》说:“哀辛方袭”,在这里也是“生”的意思。
5比干:商纣王的叔叔,因强谏被杀。《史记·殷本纪》载:“比干曰:‘为人臣者,不得不以死争。’乃强谏纣。纣怒曰:‘吾闻圣人心有七窍。’剖比干,观其心。”后以“心生七窍”形容天资颖悟之人。
6西子:即西施,春秋越国战败后送给吴王的美女。传说其患心痛病,《庄子·天运》有“故西子病心而颦其里”。
[异文]
起首两句,甲戌本作“两湾似蹙非蹙罥烟眉,一双似□非□□□□”;己卯本作“两湾似蹙非蹙罥烟眉,一双似笑非笑含露目”;庚辰本作“两湾半蹙蛾眉,一对多情杏眼”;蒙府本、戚序本作“两湾似蹙非蹙罩[罥]烟眉,一双俊目”;甲辰本、程甲本作“两湾似蹙非蹙笼烟眉,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”;杨藏本先作“两湾似蹙非蹙罥烟眉,一双似愁生愁之俊眼”,后点改同程甲文字;舒序本作“眉湾似蹙而非蹙,目彩欲动而仍留”;列藏本作“两湾似蹙非蹙罥烟眉,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”。以列藏本文字为最佳。
“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”,意思是:林黛玉清淡的眉宇之间蕴含着一丝薄愁。黛玉的愁怅来自打小的体弱多病,也来自幼年的丧母之痛,更多的则是来自与生俱来、多愁善感的敏悟。
“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”,南朝梁·萧詧《咏百合诗》有“含露或低垂。从风时偃抑”的句子;唐人刘禹锡《忆江南》有“丛兰浥露似沾巾“之句。前人的诗词,用拟人的手法来摹写花草的形态;曹雪芹则用花木含露来譬喻黛玉眼睛的润泽。“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”,即说黛玉有一双稍露伤感晶莹润泽的眼睛。眼乃心之苗,人物形象塑造,眼睛是占首位的。《世说新语·巧艺》记载了大画家顾恺之的一段韵事:
(顾恺之)画人,或数年不点目精。人问其故,顾曰:“四体妍蚩,本无关于妙处,传神写照,正在阿堵中。”
宝玉从这双眼睛里看到了什么?恐怕不仅仅是忧郁善感,我想宝玉读懂了全部的黛玉——灵秀敏悟、质真自然、清泠孤高,甚至还有固持执著。
“态生两靥之愁,娇袭一身之病”,这两句的意思是:面带清愁愈显婉转姿态,身弱多病更增姣妍气韵。“泪光点点,娇喘微微”就是目光晶莹忧伤,呼吸细微芬芳。
苏轼《鹧鸪天》说“照水红蕖细细香”;刘禹锡《忆江南》有句“弱柳从风疑举袂”。“闲静似姣花照水,行动如弱柳扶风”,这两句不仅仅叙说林黛玉动、静姿态宛然美好,同时也彰显了黛玉的大家风范、闺秀气质。
“心较比干多一窍,病如西子胜三分”,末二句写贾宝玉眼中的黛玉:聪敏颖悟胜过比干,身体娇弱过于西施。作为读者的我们,读到这里却会为黛玉暗暗揪心——心思绵密必定劳神,身体娇弱恐非寿征。悲剧的种子,在这里已经播下了。
林黛玉进贾府,已经有了一次容貌描写:
众人见黛玉年貌虽小,其举止言谈不俗,身体面庞虽怯弱不胜,却有一段自然的风流态度……
只是在“众人”眼中,还不能凸显黛玉之美。及至宝黛初会,曹雪芹用“重出”笔法,以知音者贾宝玉的视角,向大家完全地展示了黛玉脱俗清新之美。贾宝玉、林黛玉二人,基于相类的审美境界、几近一致的生活态度,相互之间产生了最大的审美认同。共通的审美体验,在瞬间迸发出高潮:
黛玉一见,便吃一大惊,心下想道:“好生奇怪,倒象在那里见过一般。”……宝玉看罢,因笑道:“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。”
这个画面的定格,注定会成为永远的经典。在这里,我们应避免作狭隘理解,即认为这种“审美认同”仅仅只是反映和体现了人的外在形貌,而无关乎人之内在精神世界。事实上,外在形貌不能脱离人的精神世界孤立存在,而人的神态、气质无一不是精神内在的外化。所以,这种“审美认同”是人的外在形貌与内在精神的合体。这种审美认同,也打破了林黛玉由于传言与王夫人的介绍而引发的“惫懒人物,懵懂顽童”的最初印象,为后文宝黛恋奠定了基础。
这篇黛玉容貌的评赞,曹雪芹运用了“神为形君,传神为主”的创作手法。这种手法的特点是忽略对象的外在具体形态,直指其精神实质。我们并不能通过“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,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”,来确定黛玉的具体面目形状,相反我们首先会感悟到黛玉多愁善感的精神内涵。传神为先的手法,也与黛玉本身的人格特点相一致。毕竟林黛玉首先是性灵、质真的诗化黛玉,其次才是身体的、世俗存在的黛玉。
《红楼梦》读者历来有“拥钗”、“拥黛”之分,实际上,钗黛在容貌、文采方面难分轩轾,但与黛玉不同,宝钗首先是世俗的、人际的,其次才衍生出文采,因而在人际存在方面,宝钗有着天然的优势。对于钗、黛的不同选择,也就是对性灵与世俗的不同选择,这种选择很直接地映射出读者的人生追求。曹雪芹对宝钗的容貌描写,便依其人格特征采取了与描写黛玉完全不同的手法,《红楼梦》第八回,宝钗第一次亮相:
头上挽着漆黑油光的纂儿,蜜合色棉袄,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褂,葱黄绫棉裙,一色半新不旧,看去不觉奢华。唇不点而红,眉不画而翠,脸若银盆,眼如水杏……
这里从衣着打扮入手,点染出宝钗具体的面貌特征,而在林黛玉的容貌描写中,衣裙妆饰都省略了,因为在黛玉至真的品格面前,这些琐碎之物全然失色。